大竹昭子桑,請告訴我照片哪裡有趣 (2008)

.
1 把照片编起来是件很累人的事。
.
—— 大竹桑编辑、执笔的
《这张照片好厉害2008》,
真的很有趣。
像这本书这样,
不知道拍摄者是谁,只单纯的看照片,
这种感受以前从未有过。
这已经够新鲜,
而那些照片本身又那么有趣。
大竹桑添附在一旁的文字,
就像是朋友在跟你搭话说:
「怎么样,这张好玩吧」,
这又是一大乐趣。
大竹: 谢谢!
—— 这本书选用的照片,
不仅有森山大道桑或中平卓馬桑那样
超有名摄影家的一张半张,
而且有90岁业余摄影师的照片,
还有3岁小孩拍到的照片,
不论职业、业余,
不管男女老少全都并列在一起,
那么首先想请您谈谈,
这些照片是怎样选出来的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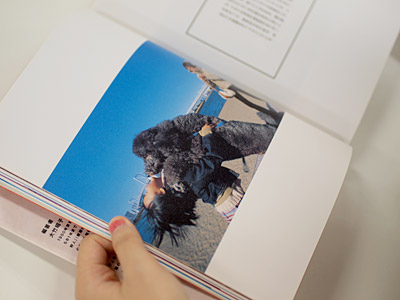
大竹: 我的选择限定在
「2007年我看到过的照片」这个范围内。
当然,一年间的照片数量很庞大,
不可能全部看过。
摄影集,相机杂志,
展览会,网络,
尽可能广泛的看了很多。
—— 从如此多的照片中选出100张,
应该是一项很费时费力的工程吧。
大竹: 100张这个数量本身就很大,
而「用同样的目光去看」也是件难事。
—— 是不是说,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,
不管作者是谁,不管是职业、业余,
也不管这照片是作什么用,
是广告,还是单纯的快照等等,
忽略所有这些信息,
全部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观看。
大竹: 比如你翻开一本相机杂志,
前面的写真页面会专门放职业摄影师的大照片,
而摄影爱好者的投稿照片会被统一放在后面。
所以在翻到后一半时,
这种页面构成会让人自然而然想到,
「这是业余爱好者的照片」。
如果是摄影比赛,
还会在意是谁选出来了这些照片。
啊,好烦!好吵!
自己都觉得自己吵(笑)。
还有一点,杂志上刊登照片时,
职业摄影师的照片放的很大,
而摄影爱好者的照片,只要不是金奖全都缩的很小。
这一点也让人头疼。
所以在看到一定数量的时候,
会压缩到300~400张左右,
再全部复印成同一个尺寸。
每天我把它们带在身上,没事就看一看,
而且常常调换照片的顺序,
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。
—— 之后又削减了三分之一。
大竹: 是的。到了大约120张的时候吧,
开始有意识的考虑照片的排列顺序,
把它们一页一页组合起来。
第一阶段大概用了一周时间吧?
早上一起床就开工。
我想,那个时间眼睛最干净。
没有前摄干扰,看什么都觉得新鲜。
此时重看前一天做的东西,经常又有新的想法,
再重新更改替换照片,真是累。
因为精神要保持集中,一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。
—— 然后大体上定下来了吧?
大竹: 嗯,没有,直到最后也是手忙就搅乱。
有些照片虽然觉得不错,
但放在书中从整体上看,
会有重复的印象,
这样的照片就没法用。
到最后的压缩阶段,几乎是
一边“呜、啊、呜、啊、”的呻吟,
一边做肝肠寸断的决断(笑)。
不过,这个组合与编织的过程,
虽然累,却是最有意思的地方。
比如书的开篇给出什么样的照片,
也会瞬间改变整本影集的氛围。

—— 最后选完的时候
虽然您是不考虑拍摄者的,
但有没有类似「那位摄影家的那张没放进去!」
这样的遗憾?
大竹: ….说实话,有这样的情况。
也挺遗憾的,
比如,有一些比较远的风景照片,
无论照片本身有多精彩,
但由于这本书的构成特点,也不好把它放进去。
这本书还是会优先选那些视觉冲击强的东西。
比如像这样的。

—— 哦,这张,确实很强。
而且简单明了。
大竹: 冷不丁一看,会吃一惊。
这是怎么拍的?
你可以随便去想象。
—— 嗯、嗯。
大竹: 即便到了颜色校正的最终阶段,
依然会发现,
嗯,这个还是有点不对劲,
然后重新换照片,重新排列组合。
因为起先只是看照片本身,
而此时放在了书的设计、排版中,
又有了不同的看的角度。
—— 是的。
大竹: 这本书在设计上,
其实也花了很大的工夫。
一页一张照片,对页是文字,
这种情况好办。
但有时为了多些变化,
想把照片放大到横跨两页,
那文字就到了下一页,
这个就烦了。
那这段文字的对页放什么呢。
如果也放照片,
就跟前一段文字弄混了。
—— 确实是个问题。
大竹: 这里,设计师寄藤文平桑,
和工作人员篠塚基伸桑,替我想出了办法。
什么也不放,只铺上颜色。
实际做出来,发现这真是很厉害的发想。
这个色彩的页面很强烈的左右了照片的印象,
在最后阶段改变了书的构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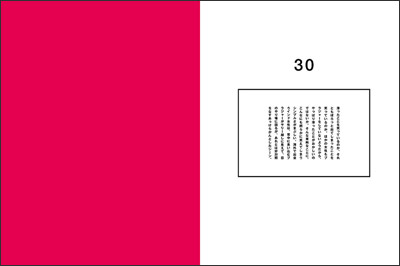
大竹: 设计上还有一个感动。
就是把文字围起来的这个框。
这本书最初的概念,
就是把照片和文字并置在一起,
但平时这样做会让文字显得更重,
局限了照片的涵义。
那把字体缩小,
又好像成了照片的注脚。
文字和照片的关系真是个很难的东西。
结果,就靠这个四方框解决了。
仔细看,每个框的形状都不一样吧。
——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。
大竹: 这是配合每张照片的纵横比做出来的。
—— 原来如此!
大竹: 这么一来,照片和文字就变的像是同级的了。
寄藤桑给出这个idea的时候,
我感动了。
就像这样,这本书
把最初的idea具现成形,
我们反复尝试反复修改了很多很多。
如何把我们对一张一张照片的
「好厉害!」的这个心情付诸形式,
怎样才能让人不感到厌倦的从头读到尾,
设计师,编辑,和我,大家齐心合力,集思广益,
虽说直到最后的最后依然手忙脚乱狼狈不堪,
但的确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体验。
(待续)
2008-11-04-TUE
.
.
.
2 怎么样,才算「好的摄影书」?
.
—— 读这本摄影集的过程中,
我会不停的想,下一张是什么?下一张是什么?
这个过程很有趣。
而且读完立刻想再重读一遍。
大竹: 啊啊,那个基本上就是拍照片的感觉吧。

—— 诶?
您的意思是?
大竹: 这些照片,
并没拍到多么特别的东西。
但之所以想再读一遍,
是不是因为被其中什么东西所吸引?
—— 是的,
有好多这样被吸引的地方。
大竹: 一边感觉到被哪里吸引着,一边看,
我觉得这跟拍照片时的状态非常接近。
比如在日常生活中,也有些东西,
会挑动你的神经让你不由自主的去看它。
—— 不仅仅,是眼睛所看见的东西,是吗?
大竹: 对对。
比如邻居围墙上窜出来的形状奇特的东西,
比如桌上的笔筒与台灯之间的距离,
比如衣架上无所事事的耷拉着的毛衣袖子。
这些东西,一眼望过去并没什么特别之处,
但实际你在看的时候,
心是在无意识与意识之间不停的摇摆的。
也就是说,心是个照相机,心的照相机在拍照片。
这时候,如果真拿照相机按个快门,
估计拍出来的照片也会很不错的。
—— 还真有可能。
听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,
每天上下班路上一打眼扫过的风景,
如果离远了拍下来,
变成「某小路上的风景」,普遍化了,
变成照片了,
就好像那地方从没见过似的。

大竹: 深有同感。
—— 这是不是说,在平时的生活中,
人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像照相机一样
一面对着焦一面看着什么呢?
大竹: 对,远些、近些、
取景、构图,等等,各种各样的看。
只不过,那些时候自己不是有意识去做的。
所以拍成了照片,一看吓一跳。
诶,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吗。
另外,气象、光线的状态等等,
也会让风景的观看变得不同。
—— 阴雨天里那种昏暗的时候,
即使是白天也多少感到空气中有一丝不安。
大竹: 也就是说,人在看什么东西时,
是有自己的心情介入其中的。
照相机只是一台机器,
它拍照是靠机械装置,
但操纵这台机器的人,
瞄取景器、事后看照片的人,
他是有自己的意识的。
所以同一个东西每次看着都不一样
—— 人们常说「心的眼睛」什么的,
实际上是你从所看的东西中感觉到什么,是吧。
大竹: 是的是的。所以说,好的照片,
连看照片的人的意识都能改变。
比如,你看完一本摄影集,出门,
眼前的风景看起来都像刚才的照片。
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?
—— 有过有过。
那时候我是以那摄影家的视线或角度去观看的是吧。
大竹: 对对。
所以说,能否引起这种变化,
也可算作判断一本摄影集的好坏的标准之一。
—— 原来如此。
大竹: 我有时候,感觉今天的街道好干净啊,
然后仔细一想,
发现是之前刚看过很好的照片。
就像那句话所说,“眼睛被擦亮了”,
真是那个字面意思。

大竹: 另外,可能有点前后矛盾,但我们得承认,
摄影集的好坏,
有一部分就是靠编纂的方法。
—— 把哪张照片放在哪个位置,
如何进行构成等等。
大竹: 极端的说,
依靠书的编写构成,
做出来的东西能超出照片的原本实力。
—— 不过,这跟那种从许多名作中精选出来的摄影集相比,怎么样呢?
大竹: 这个啊,很不可思议,你能看出来的。
是由少量照片编成的,
还是从森林一般的照片堆中挖出来的。
怎么说呢,它们散发出的能量是不一样的,
视线的密度是有差距的。
—— 啊啊,果然。
大竹: 照片这种东西是极敏感的,
它有种与生俱来的暧昧。
要问这种暧昧是从哪儿来的,
我觉得最终是来自人的意识的那种含含糊糊。
这种「含含糊糊」是决不可能追根究底的。
所以说,暧昧是照片的宿命。
如果舍弃了这一点,照片也就不再像照片,
不再像是人做出来的东西了。
(待续)
2008-11-05
.
.
.
3 妄想也自由。
.
—— 这本书的每张照片都附有大竹桑的文字。
这些文字里,
有时能看到大竹桑的妄想,
作为读者我很喜欢那些。
是否可以说
那是大竹桑在看照片时的一种自成一派的游戏呢?
大竹: (笑)我啊,有妄想癖,
流露出来了是吧。
妄想、臆想,已经内化为体质的一部分,
无法自拔了。
—— (笑)是不是说,看到照片的一瞬间,
脑海中就已经浮现出各种妄想?
大竹: 是的。不是有意去妄想的,
是不由自主的,
自然而然它在自己眼中就是那个样子!
而且,一旦把它看成那个样子,
那形象就会进入自己的内部。
小时候落下的毛病。
—— 不过大竹桑的妄想,
决不是单方面一厢情愿的。
我们能很清楚的感受到,
大竹桑是自由的穿梭在妄想与现实之间。
而且,您看照片的方法也十分的自由。
比如,这张空中飞人,
就让我感到您看照片真是非常自由。
在所附文字中,
您不是写到把照片颠倒过来吗。

这是猎头公司的转职广告所用的照片。
实实在在的传达出“不要错过机会!”的迫切,
同时也感觉到换工作的高度风险。
或许作者是为同时传达这两层含义而使用了空中飞人,
但若把它颠倒过来,
把原本伸手接纳的男人看作是飞身向上的角色,
则似乎更能感觉到转职者的拼命。
另一方面,转为伸手接纳角色的男人,
不见其面容,肢体舒展,宛如从天而降的「神」。
(摘自本书,大竹桑的文字)
大竹: 啊——,这张。
我经常把照片颠倒过来的。
不止照片,别的东西也经常颠倒着看的,这么说来。
我喜欢尝试着从其用途以外的角度去看一样事物。
—— 肯定也跟您把照片复印成纸张,
平时总把那么一叠纸带在身上有关系吧。
大竹: 确实是这样。
如果是厚厚的摄影集,
就不那么容易颠倒过来看。
可能是B5这个尺寸好。
另外,要说这张照片为什么颠倒着看,
我是觉得把两人角色调换之后更符合转职的感觉。
虽说衣角垂向的方向不合理,
但你不觉得颠倒之后,
看着更像那么回事儿吗?
—— 好像确实是。
颠倒过来看,戴领带的人的衣服翻起来的地方,
就好像在诉说着他换个工作有多拼命。

大竹: 对,拼死拼活的,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了。
—— 这个「颠倒」,
真的让我大吃一惊。
以前看照片从没想到过这一点。
而且让我明白了,原来看照片时是可以这样玩的!
自己的感受也变得十分的自由了。
大竹: 如何看一张照片,是无所谓正确答案的。
这不是语文考试。
你随便怎么想都可以,
即使跟作者的意图相违那又怎样呢。
平时的生活中这种事多了去了。
比如,是不是有好多东西,你只看它的形状,
是完全看不出其用途的?
—— 确实。比如第一次见到青竹踏,
可能会想,这什么东西。
大竹: 青竹踏属于日用品,可能还好。
比如施工现场的设备,如何?
每天去车站的路上都能见到,
那是什么东西呀,
意识的某个角落总有所牵挂,
但从没往深里想。
这样东西蛮多吧?
—— 这么一说还真是。
大竹: 今天你回去时,记得去看一看,
有些地方在走过的一瞬间心里会想,真怪,
这样的地方肯定要多少有多少。

到处可见的人家的玄关口。
大白天,没有人影,只停着自行车。
看不出要拍什么,没有头绪。
尽管如此,你发现,门恰到好处地藏在台阶后面,
近处的植物从则模糊一片,
看着看着,
空气中散发出不祥的气息。
妄想,总是从日常的缝隙中偷偷钻过来。
(摘自本书,大竹桑的文字)
—— 在自己没去意识的地方,潜藏着视觉性的奇观。
大竹: 对,存在着视觉性的钩子(hook)。
心为之所牵,意识便产生了摇摆。
明白这一点后,再去看什么东西,
就能够进行各种对话。
我觉得这就是与照片进行对话的基本。
或者反过来,
某个瞬间你发现有些东西并非你一直以为的那样。
比如你看一个院墙,
一直以为那是某一人家的东西,
但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那是两户人家的院墙贴在了一起。
—— 啊啊,唔,唔。
大竹: 那么,为什么,
当时把这两层院墙当成一个了呢?
心里怀着疑问,重新去仔细观察那墙,
然后你会发现,
那里存在着一些诱导你把两个看作一个的视觉性的理由。
比如两户人家的墙都接近炼瓦色(sRGB:#9C4836)。
—— 颜色接近,所以看成了一个。
大竹: 颜色之外,比如形状,光、影,污点,等等等等,
你会突然发现,
原来还有这么多因素。
即使是很细微的地方,只要一直盯着它看,
就会扩展为广大的世界。
所以首先要做的,就是
「对那个正在看着什么的自己有所意识」。
有时妄想,
有时感到温暖,
有时还能进入非现实的境界。
你追询着你与你眼见之物的关系,
从中领悟为何你产生出这许多情感、感觉。
我想,这样一来,看照片这一行为就变得更自由,
也更有趣了。
(待续)
2008-11-06-THU
.
.
.
4 没法把摄影当做工作。
.
—— 大竹桑,您有一段时期,
相当热情高涨的拍过照片吧。
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?
大竹: 1979年在欧洲旅行了3个月左右,
然后到纽约,暂时住了一阵子,
就在那时开始的。
但我并没有「学过」摄影。
—— 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没拍吗?
大竹: 顶多拍拍纪念照。
相机也是傻瓜相机。
怎么说呢,在外旅行的时候,
似乎不太愿意拍照片。
—— 是希望把风景烙进自己的眼睛里,
而不是照相机。
是这个感觉吗?
大竹: 也许是的。
那时,一定是自我意识过剩吧。
年轻的时候嘛,
都会把自己的体验看的很重。
仿佛如果拍了照片,
感受就被相机代替了似的。
—— 自己的体验就削弱了的感觉吧。
大竹: 对对。
那种十分浓密的感受,
一旦收进取景框,
似乎瞬间就微不足道了,
这个让我受不了。
或者类似于看画展,
如果看的感动了,反而不愿意买印了画的明信片或图录。
总觉得差那么一些。
所以旅行没拍什么照片,结束后去纽约,
开始了漫无目的、随遇而安的生活。
当天的日程当天早上决定。
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在自己的内部,
摄影已经在逐渐积攒起来,呼之欲出了。

巨大的洼地。
但不是自然的产物,
大概是石矿开采遗留下来的痕迹吧。
开采后变成垃圾堆放处,
现在也用作放牧场,
从中部的牛马群可以看出来。
紧挨着它们的,像是低收入者所住的棚户区,
再往上一层,排列着时间更早些的稍好一点的砖瓦房。
一个场所的前世今生,
被这样纵向的图解着。
(摘自本书,大竹桑的文字)
—— 实际开始拍照的契机是什么呢?
大竹: 纽约,
是个很容易让人对摄影亲近起来的环境。
有很多摄影画廊,
ICP(国际摄影中心),
MOMA(纽约现代美术馆)等等,
有好多可以看照片的地方。
现在的日本也是这样,
但80年代初还很少有展出照片的地方,
所以在纽约,第一次感觉到摄影就在身边。
另外,还有街道的那种锐角的光线。
我觉得那个能让人产生拍照片的冲动。
一回过神,发现自己想拍照的心情已经无法遏止,
于是就像领受天命一般
跑去买单反相机去了。
—— 原来是这样(笑)。
选相机的时候没有什么纠结吗?
大竹: 我那时一窍不通,
找懂相机的朋友来帮我选了。
然后就如痴如醉。
我小时候,
是那种有许多无意义的举动的孩子。
经常被呵斥:「别老干这些莫名其妙的事!」
但摄影,你就可以拍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想拍多少拍多少。
这真是巨大的欢喜,让我痴迷到不行,
简直觉得人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吧。
买相机是在秋天,
那个冬天是个大冷冬,
但我热火中烧,一点儿都没觉得冷。
—— 这可正是「忘我」的境界!
大竹: 而且我拍照片的地方,
净是些不能把相机露出来的危险的地方,
我把相机藏在羽绒服里,
只在拍的时候拉下拉锁放出相机,
就跟间谍似的。
—— 拍的是彩色吗?还是黑白?
大竹: 黑白。
同时也开始了暗室的作业。
—— 暗室也!
大竹: 对。
有厌倦了摄影的人把工具让给了我,
我就等天黑,做在地上弄。
—— 那股兴奋劲儿持续到什么时候呢?
大竹: 圣诞节期间是最高峰吧。
那时有许多派对的邀请,
如果有搞摄影的人我就去,没有就无视,
摄影基本就是一切的判断标准了。
—— 去派对时,是聊摄影吗?
大竹: 把自己的print拿给别人看。
问人家觉得怎么样。
现在想,那时真是天真无邪。
就这样冬去春来,
与摄影的恋爱持续了一年左右,
然后,蓦地出现一个想法。
「摄影这东西,可不得了」。
就这么一下子看清了。
摄影的本质,或者说摄影的艰难。
这东西如果当真了可不得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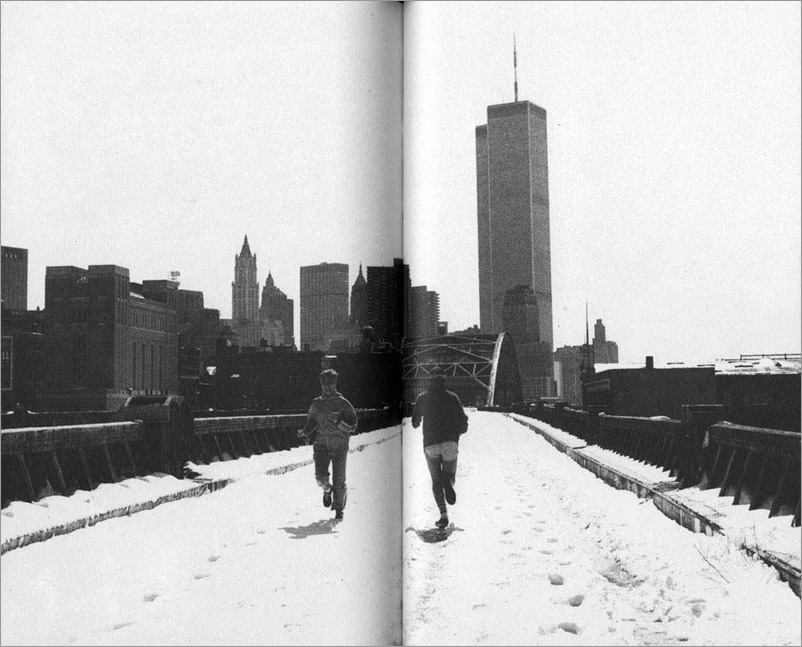

大竹桑在纽约时拍的照片
(选自大竹昭子著『アスファルトの犬』)
—— 是什么那么不得了呢….。
大竹: 需要一直等待,
或者说要把运气引向自己,这很难。
自己对自己下手,这很难。
比如,写文章,
写多了水平会有所提高,
思考也会有所深入,
总会有种积蓄下了什么的喜悦吧?
—— 是说自己会被自己的提升所激励吗?
大竹: 对对,若有所悟的时候,会有喜悦,
但在摄影,更多时候这种积蓄反而有相反的效果。
因为只要按按快门,
只要有点感觉,初学者也能拍到好照片。
但当我明白了这一点,
开始时的兴奋与心动就渐渐消失了。
那时我心想,
之前我已经感觉过最佳状态,
那从今往后就要走下坡路了吧。
但如果还想继续摄影,
你就不得不想办法把自己重新初始化,
这意味着你要朝着与「圆熟的境界」相反的vector(方向)走。
心想,这可是很厉害的事。
—— 作为工作的摄影,完全没考虑过吗?
大竹: 虽然作为职人去拍照片也是种选择,
但我觉得不适合自己。
—— 那是为什么呢?
大竹: 与摄影的相遇,从一开始
就正中strike zone(好球带)的正中央。
类似「这就是摄影」的感觉,
我看到了这种太过本质的东西,
所以就只能非此即彼。
一面完成作为工作的摄影,
一面去拍自己的照片,
我也没有那个能力,
于是就想,这东西做不了谋生手段。
摄影与生存,
像银纸一样紧贴在一起撕不开,
所以如果要不失动力的持续下去,
没有相当的喜欢是不行的。
这种媒体,容易开始,也容易放弃。
所以,对那些持续着自己的摄影的摄影家们,
我是怀有相当的敬意的。
能感受到他们的生命的狠劲儿。

—— 关于摄影,从没这么深入的思考过。
真是意外收获。
(待续)
2008-11-07-FRI
.
.
.
5 窥视与欲望。
.
大竹: 照片就像「活物」一般,敏感细腻,摇摆不定,
所以拍照的时候不把意识放开是不行的。
稍有一点精神不振,信心不足,决断力不够,
立刻会显现在照片上。
那样的日子,就是拍不了照片的日子。
—— 心如果没有打开,
就没法跟被摄体形成交流。
大竹: 要么,干脆彻底封闭,
看世间是一片彻底的黑暗,
那样倒也….
—— 也可能自成一格。
大竹: 森山大道桑有个拍樱的系列「樱花」,
是最低谷的时期拍的,
就有种封闭了的狠劲儿。
但在夏威夷岛,
同样是森山桑的照片,
就感觉不到心的封闭。
反而能感觉到直接切入本质的激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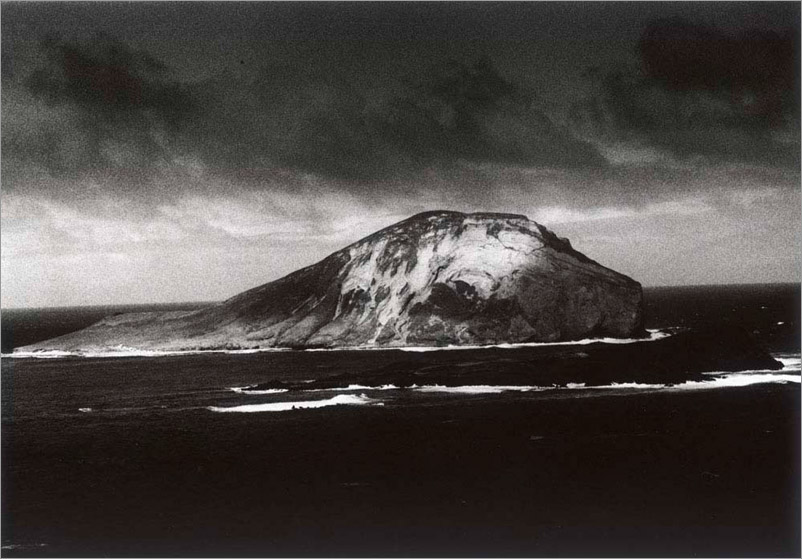
大竹: 这就是说,摄影家必须「时刻保持着身心的开放」,
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—— 啊,确实….。
不仅是心,还比如身体状况之类的,
有好多不能随心所愿的地方。
大竹: 摄影家就是这样一批人:
做不到的时候就是做不到,必须承认和接受。
除此之外,比如天气的变化,
比如被拍一方的心情好坏、一而再再而三的计划变更,
不能随心所愿的地方还有好多好多。
—— 是啊。
大竹: 必须随时应对各种变化。
不过,真正厉害的摄影家,
甚至能改变天气的!
—— 听说过。
嘴里嘟囔着「明天,要是下雪就好了」,
于是真下雪了。
大竹: 对。可能听起来有点邪,
但真正有才能的摄影家,
能够将自己「媒体化」,
做到森罗万象与能量之间的交感。
「媒体(media)」的语源跟「灵媒」是一样的,
也可以说,他们就是一种「灵媒师」。
—— 原来如此!
大竹: 然后,说一个我个人的观点,
我觉得,不够性感的人,摄影也是不行的。
好的摄影家,到底是有种情色的魅力。
即便是简单聊几句,如果感觉不到这人的性感,
那照片也不用看了,可以直接想象得到。
—— 我想到一点,也许跟您说的没什么关系,
但我发现摄影师这个人群,总是特别受异性欢迎。
娶的老婆也经常是大美女。
大竹: 啊,是这样啊。受欢迎的——。
摄影的原动力,是「欲望」。
是欲望驱动着摄影行为。
所以受欢迎也是理所当然了。
—— 瞄取景器这个行为,从某种意义上,
也能算作偷窥。
大竹: 对,窥视与欲望是不可分的。
当摄影师把人心中的本能、原初记忆等等引出来,
定着在照片上的时候,
看照片的人会「噢——!」的产生共鸣。
所以,拍摄者的心的跃动很重要。
心无所动是不行的。
心有所动,并诚实的映在照片上,
就会单刀直入的捣进观者的内心。

虚化了背景,
只把竹笋放在正中间拍。
被摄体很平常,
可直球strike的拍法不平常。
我是竹笋,你有意见吗?这迫力,
仿佛竹笋自身在拍它的伙伴,
有种没法当作他人之事的说服力。
(摘自本书,大竹桑的文章)
—— 拍摄者的心绪介由照片传达出来,
自己看了也会恍然大悟吧。
大竹: 对对。
然后,在看到这种照片的时候,
我喜欢去想,这张照片是哪里牵动了心弦呢。
—— 例如,会想哪些事情?
大竹: 牵动心弦的照片,
总有些未知的部分。
能感觉到某些异于平常的看事物的方式。
—— 这张照片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眼球,
开始时觉得好可爱,
可仔细一想其实挺残酷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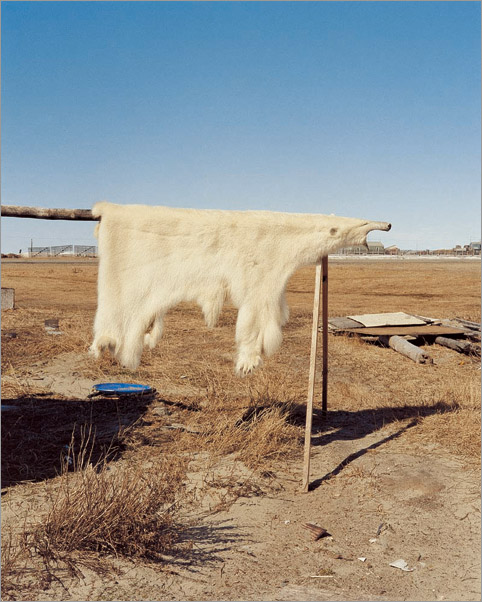
大竹: 是啊。
胖胖的北极熊被晾成了干儿。
悲剧与滑稽的同行。
—— 后来才知道,
这是石川直樹桑的照片。
碧蓝的天,和空旷旷的感觉很像他的风格。
大竹: 被摄体是放在正中央拍的吧。
我就想了,是什么让这张照片得以成立呢。
被晾起来的北极熊当然很可爱,
但我觉得这张照片,
起决定作用的是「距离」。
你觉不觉得,
稍微后退一点,或向前靠近一点,
都会破坏现有的这种微妙的平衡?
—— 唔,唔。
没注意到,
拍摄者与被摄体的距离也很重要啊。
大竹: 十文字美信桑的这张,
我觉得也是「距离的照片」。

—— 啊,这张,真不错——!
这张我一直记着。
起初目光被白衬衫吸引,
然后就弄不懂整体的构造了。
大竹: 对对。首先白衬衫映入眼帘,心想,
啊啊,两个大叔;
再移动视线,发现
「啊!手握在一起!怎么回事?」
—— 两个大叔,衣着也很正式。
手与其说是握着,
其实是压着。
还能隐约看见钥匙似的东西….。
这是怎么了?心里很觉不可思议。
大竹: 我问过十文字桑,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。
—— 这场景连拍摄者自己也弄不清楚啊。
大竹: 地点知道,是在他下榻的宾馆的休息厅。
在这宾馆里….
—— 是偷拍啊。
大竹: 对。一开门,
这光景便映入眼帘。
靠近到不被他们发现的极限距离按了快门。
—— 如果给手的部分一个特写,
反而会产生多余的含义。
大竹: 是啊。反过来也是,
如果离得再远一点,就变成了风景照片。
—— 就变成了:某房间的风景。
大竹: 但靠的太近被发现了就完蛋了,
有种呼吸加速的紧张感。
观者也进入到拍摄者所在场面之中,
随着拍摄者一同紧张:
他们要是转过身来可就糟了。
看照片的时候,
我们一般是从安全的地方望过去;
可这一时空的阻隔很容易就崩塌了,
眼前的日常,便与照片中另一侧的现实
连在了一起。
我想,这就是我被这张照片吸引的理由。
(待续)
2008-11-10-MON
.
.
.
6 是什么支撑着看照片这一行为。
.
大竹: 我觉得,如果是日本的读者,
看『这张照片好厉害2008』有所共鸣的地方是共通的。
—— 是说拍照片的一方和看照片的一方都是日本人?
大竹: 对。其他国家的人看了这些照片,
就完全不一样。
前几天,给欧洲的年轻女性看了这张照片。
她的反应很出乎意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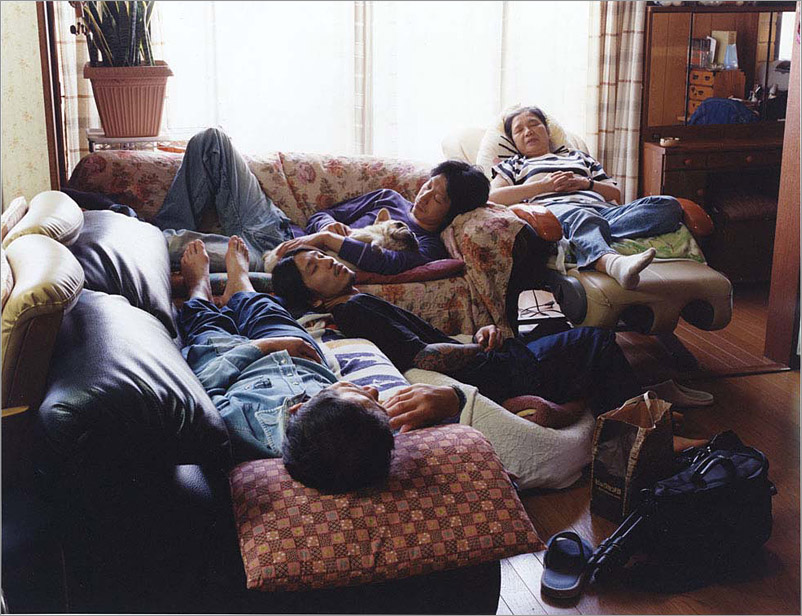
大竹: 这是名叫浅田政志的摄影家的系列作品的一张,
该系列先设定好场景,摄影家自己与家人共同出演和拍摄。
如果是日本人,看了立刻就知道这是起居室吧?
—— 是,很难想象成别的。
大竹: 在起居室睡成这个样子,
大致能猜到这是家人吧。
—— 像是家人。
至少也是关系很近的人….。
大竹: 但那个欧洲人说,这是
「中国的阿迪达斯之类的工场工人们
在休息时间酣睡着的场景」。
—— 哇….(笑)。
大竹: 「诶——,这是为啥」….
同时又觉挺有趣。
—— 即使是看同一张照片,
不同的人看竟差这么多。
大竹: 还有别的例子。
这张守夜的照片,对这张的评论也很怪。

大竹: 我说「这是守夜的场景,
觉不觉得有种奇妙而且安心的感觉?」
她说「一点儿都没有!」「失去了老伴儿,
老奶奶要多悲伤!除此之外想不到别的」。
这差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
当然,即使同是日本人,
每个人感受方式不一样,不可能规定一般的标准,
但从这张照片,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仅是悲伤吧。
还能感觉到平和的东西吧。
—— 有的。死与生连接在一起的那种安心感。
….而且,说句不检点的,
看这张照片,甚至觉得有点好笑。
大竹: 诚实的感想!
忍俊不禁,或者说会心一笑。
与死去的人合个影,
想法本身就有点出奇。
—— 拍照的人,也稍微有点笑了….。
大竹: 对,尤其是孙子辈的,在微笑。
在守夜的场合该如何表现,他们还不太摸得清,
拍这张纪念照作为告一段落的标志,
大家也整理好了自己的心情,
自然的浮现出笑容。
—— 告一段落的笑容。
大竹: 看这张照片我想到,
拍照片这一行为,
有种改变场面中的空气的作用。
—— 嗯嗯嗯。
确实。
大竹: 参加聚会,经常聚会本身无聊,
但一说「合个影吧——」,大家凑到一起,
心情就突然放松了,气氛也活跃起来。
大家开始说说笑笑,
感觉到今天确实存在过。
事后拿不到照片也无所谓,
以拍照为契机,所造成的那个场面的气氛的变化,
这个有意思。
—— 是啊。
合过影之后,人们似乎变的更近了。
大竹: 说到守夜的照片,还有一张。
—— 是的。这张我也喜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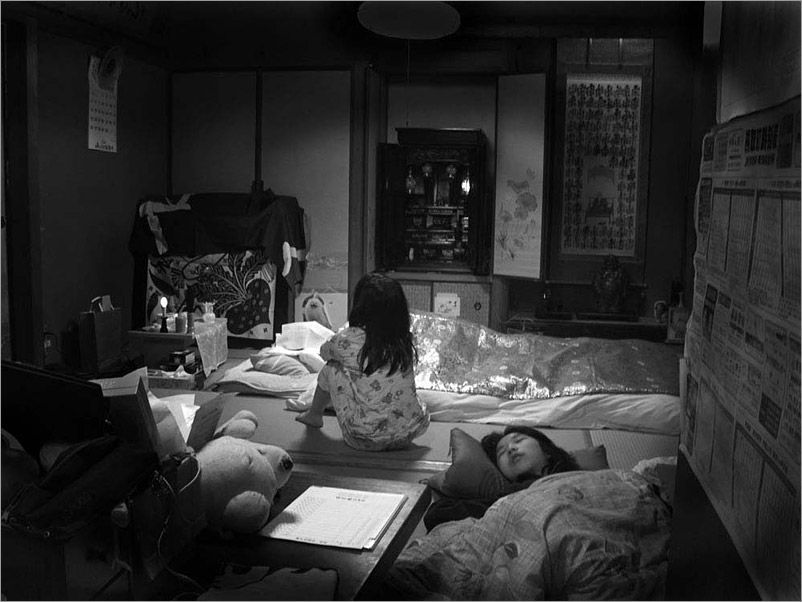
守夜,孩子一个人醒着,
看着去世的奶奶。
这也许是第一次经历身边的人的死。
时间的裂缝中漂出不同于以往的时间,
让房间的颜色变的不再熟悉。
少女用皮肤感觉着,
抱着膝,等待那种无法言表的东西充满全身。
也许明天就会忘记,
但贯穿她的一生,将会反复重现,
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预感的一刻。
(摘自本书,大竹桑的文章)
大竹: 奶奶去世的夜晚,
大家都睡了,这孩子却醒着。
—— 对,看不见表情,不知道在想些什么,
但抱着腿坐着,估计坐了很久了。
大竹: 关于这张照片,欧洲女人的看法也全然不同。
她说「感觉她似乎抱有杀意」。
—— 诶——!真是不一样啊。
有点吓人的想象。
这跟西方人不晓得佛龛有关吗?
大竹: 有可能。
日本人看到这个场景,
瞬间就知道这是守夜,
所以不可能想象这孩子怀有杀意,
但如果搞不清这个状况,
只是看到她的背影,和眼前横躺的人,
也许一瞬间感觉到杀意也不是不可能。
—— 真没想到。
看到的差这么多。
大竹: 文化,地域,世代….。
每个人生长的背景不同,
观看方式也有差异。
不止是简单的本国外国差异的问题,
即使同是日本人,
估计也能发现意想不到的差别。
平常过日子可能意识不到那么多,
但把照片放到你我之间,
那就是可能的。
这本书,若能成为与家人,或友人、
恋人等等亲近的人的交流的契机,
那是最棒不过了。
(待续)
2008-11-11-TUE
.
.
.
『这张照片好厉害2008』(朝日出版社刊)这本摄影集很有趣,
我们与担当了编辑和执笔的大竹昭子桑进行了访谈。
这本摄影集里,大竹桑从2007年看过的照片中
不问职业•业余的选出100张,
并给每一张写了一段简短的文字。
照片的页面,没有拍摄者名称,也没有标题,
次页是大竹桑所附的评论,
说是评论,却像是朋友间闲聊,
「喂,这个,好玩吧!」那样的感觉。
「ほぼ日」(网站名称)虽然既喜欢拍也喜欢看,
但对于所谓的「发表了的照片」,
总觉得把感想付诸语言是件难事。
不过,学会了大竹桑的观看方式,
也许照片会变成更「有趣」的东西?
.
.
.
7 用照片聊一聊。
.
—— (啪啪翻着画册)
这个第56号照片,
读过大竹桑的文字,
我会介由照相机,游移在
被拍的男性与看着他的自己之间。
不停的切换视线。
能够把这种运动付诸语言的,不是摄影家,
这是看照片的人,书写的人的乐趣。
真是很棒。

少年忘情的从陡坡上下来,
一旁,藏在暗处的摄影者则投入的偷窥着这一幕。
二人同处一处,
脑中所想却完全不同。
这是张一瞬间让人明白这一切的照片。
看着照片,
涌上一种误闯了犯罪现场的不安感。
(摘自本书,大竹桑的文字)
大竹: 摄影的理论或本质,
已有数量繁多的书籍阐述过。
但大多是晦涩的语言、概念、
欧洲哲学书的引用等等的大汇总。
—— 是的,难懂的内容挺多的。
大竹: 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,
我们的意识、情感所发生的变化,
就像前面所讲的,
全然不是什么难懂的东西,
而是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。
但为什么一想要把它讲出来,
就变得这么难呢,
我一直抱着这个疑问。
所以,在配文字时我首要注意的,
是把照片置换为我们的日常体验,
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。
—— 而且有很多东西,
是用语言表达出来之后才明白的。
而且,所用的还是浅显的语言。
大竹: 说到刚才的56号照片,
把一张照片放在眼前,
拍照片的一方,被拍的一方,
看着这二者的一方,
像这样我们是一面在各种立场中切换,一面看着照片。
—— 这样,在看照片的时候,
我们就能扮演每一种角色。
大竹: 对对,
看的时候,除了观者自身的视线外,
必然还要进入他人的视线之中。
只不过我们意识不到。
围绕着这各种各样的看的体验,有无数无意识的碎片
充斥在照片之中。
所以我尽量挑选出各个种类的照片,
书写的内容也每一张一换。
——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个企划的?
大竹: 想做一本把照片和语言并置在一起的书,
这个想法很久以前就有。
但单纯的文集又比较无聊,
就打算有意识的加入一些谁都没做过的东西。
—— 比如什么样的?
大竹: 对职业摄影师与业余爱好者的照片不作区分,
就是其中之一。
因为我认为,不作区分,
能够让摄影的本质得以显现。
而且也不管它是昆虫照片,还是旅行照片,还是什么别的,
我有意识的去消解摄影内部的门类。
还有就是不在照片页标注摄影家名。
这也是我的一个坚持。
照片处于「无名」的时候,
与照片本身的相遇会更容易。
日常生活也是,
半敞着门的人家,
是不是比挂着漂亮名签的人家更容易进?
名字有时会成为一种权威,
掩盖事物的本质。
而且,人们看事物的时候,
已经养成了依赖于各种外部线索的习惯。
我想试着拿掉那些辅助,
干干净净的面对照片。
—— 您配的文字都蛮短,
但每一段文字,无论内容还是写法都不尽相同,
这一定是很辛苦的工作。
而且您的文字里完全没有那种
经常在摄影文字中见到的「批评」。
大竹: 一般情况下这类文字,更多是评判照片的成功与否,
或是对所拍内容进行说明。
但我们在看一张照片的时候,
或者妄想,或者感情移入,
或者天马行空的回忆,等等等等,
我们的内在的反应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。

看到这张照片的瞬间,脑海中浮现出
小时候收到的北海道特产マリモ羊羹。
就是这些蒙了一层褐色,变了模样的保龄球。
裹着胶皮的球状物,用牙签一戳,
羊羹瞬间从破了的皮中冒出来,
类似那个感觉。
废墟有种能容纳无论什么想象的宽宏大量,
而拍成照片,失掉了原有尺寸,
imagination可以无限的扩展开去。
(摘自本书,大竹桑的文字)
大竹: 比如这张照片。
散落一地的保龄球,
但在我眼中,
就成了マリモ羊羹!
—— 很明白您的感觉。
颜色和形状,的确是マリモ羊羹啊!
但实际的大小和マリモ羊羹相差很多….。
大竹: 是的。我想,在拍摄现场
是不会产生マリモ羊羹的想象的。
但照片拍出来一看,
感觉就像了。
这之中就有照片的一个谜。
看照片的时候,人会一边看
一边在脑中自由自在的改变其中的大小。
形,色,空气感,纵深….
断片式的image,在人的脑中
建构出子虚乌有的story。
—— 嗯嗯嗯。很有趣。
照片这东西,暴露出
我们究竟是多么奇怪的生物。
这本书,纸张、印刷、装帧也有点不一样。
照片和书的氛围,有种整体的统一感。
大竹: 不望它太咄咄逼人,
而是要那种糙糙的感觉。
摄影集,如果搞的太隆重,
本身就会让看的一方感到拘谨。
所以我想做成不那么高冷,而像是溶解到日常之中的,
同时又对看的人有强烈的诉说的装帧。
这也要归功于寄藤桑的团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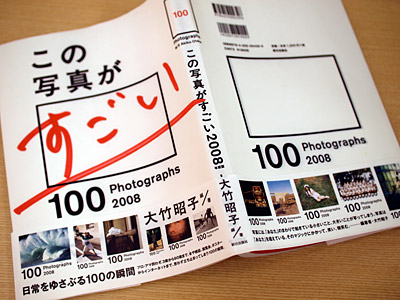
—— 有了这本书,所谓的摄影集
就变得挺平易近人的。
大竹: 谢谢。
我就想啊,
大家拿着照片七嘴八舌聊一聊,
那感觉跟一起吃顿饭蛮像的。

—— 大家借着「饭局」这个媒介,
能生出好多会话。
这个真好吃,之类的。
真是,只要能吃顿饭就没问题。
大竹: 但其实比如小说、比如绘画、电影,
也是一样的。
这些就像是孕育着交流(communication)的胚芽。
尤其照片这东西是没有答案的,
你怎么样说都可以,这个最棒了。
—— 正因为没有答案,
所以更能畅所欲言。
大竹: 对对。
不用管那么多,有什么感想就怎么说。
这本书里有张澤田知子桑的照片吧?

大竹: 这张照片展示在眼前,
两个阿姨开始聊了,
「你看这个,是一个人?」
「诶——,不是吧!」
「但瞅着就像一个人啊」
我就见过这样的场景。
说的东西没什么深意,但谁都会那么想一想。
—— (笑)。确实这照片让人忍不住想说一嘴。
大竹: 对,不要怕,试着付诸语言,
渐渐让感觉获得解放,那就好。
另外,这本书说到底
只是我个人所认为的「厉害照片」100张,
「厉害」的标准每个人肯定不一样,
大家自己试着作一个100张选辑肯定也不错。
而且,比如可以把它当做摄影workshop的教材,
在学校里让学生们哇啦哇啦讨论讨论,
我想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用法。
—— 用法可有100种呢!
这么说,本书的标题里有「2008」,
明年也有预定吗?
大竹: 暂时是这么打算的。
—— 哦,好期待。
多亏了大竹桑,
看照片从此变得更有趣了。
感谢您这7回连载的陪伴。

(终)
2008-11-12-WED
.
.
.
译 / 蔡骁